学术新论 | 刘复生:关于“宋学”与“儒学复兴”
发布时间:2023-04-13 1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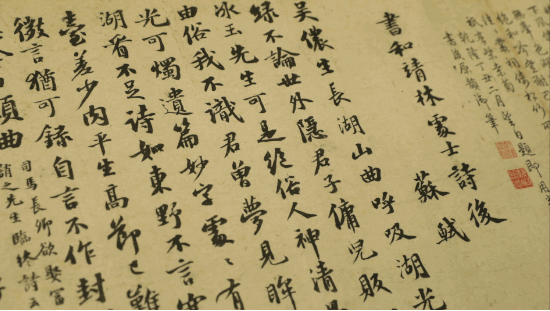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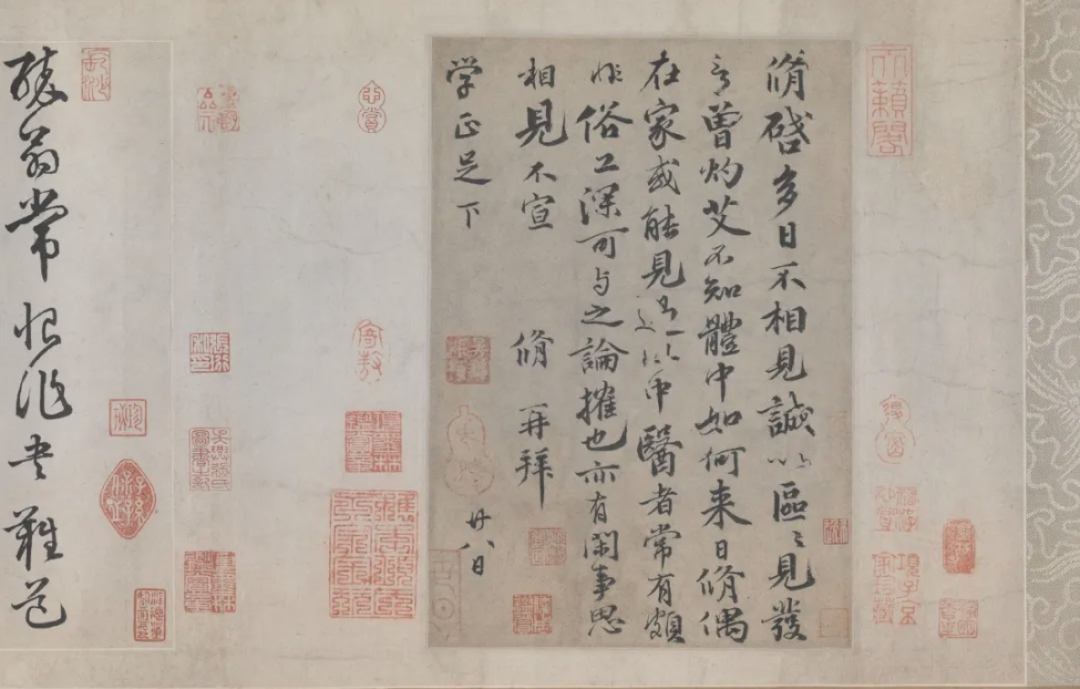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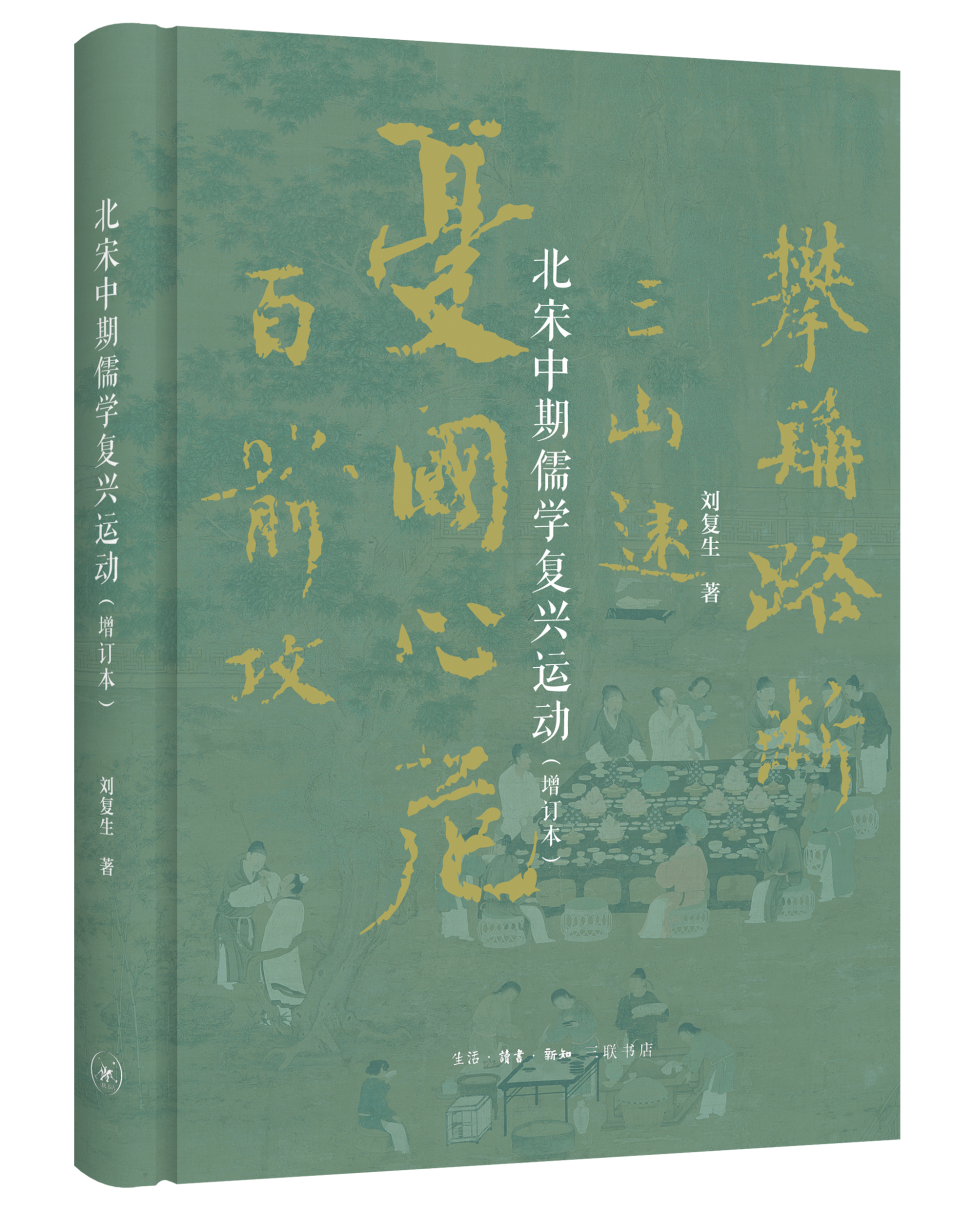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
- 上一条: 东西问| 张帆:古DNA如何破解“人类从何而来”? 2023-04-10
- 下一条: 刘德增 | 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 2023-04-21
友情链接
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四川大学) 版权所有 如有问题和建议请联系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四楼 邮编:610064
Tel:8628-85417695 Fax:85417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