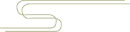《历史研究》| 赵宇:金至元中叶北方儒士群体的思想转型
发布时间:2023-04-03 10:38
摘 要:金代至元中叶,北方儒士群体存在一场从“文”到“道”的思想转型。在科举制度层面,金元时期北方进士科目经历了从策论到经义的复兴历程;在思想学术层面,金元时期的北方儒学出现了从标榜“学道”到接受道学的演变。金元北方儒士群体在思想与身分上的传承,是推动元中叶延祐复科的关键力量,其思想转型与唐宋时期的思想转型有诸多共通之处,实为唐宋思想转型的另一条轨迹。两条轨迹共同证明,程朱理学而非苏学等学说发展成为宋代以降主流儒学并非偶然。唐宋时期的诸多历史变迁历来备受学界关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在思想史领域,包弼德(Peter K. Bol)基于“文”(主要是古代文化学问)与“道”(主要是道德思想学问)两种概念,提出了有名的“唐宋思想转型”说,即古代中国的士人文化在唐宋时期大致存在从“文”到“道”的思想转型。包氏认为,与具有多样性特征的苏学等学说相比,程朱理学原本与8世纪以来的主流思潮“格格不入”, 其在后世成为正统官学并非唐宋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在包氏前后,尚有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论说唐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问题,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学界大体认同唐宋时期确实存在重要的思想变迁,值得深入探研。论及思想变迁,同一时期的科举制度演变不能不予以重视。苏轼曾论述科举制度与学术思想的互动关系: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
苏轼道出诗(词)赋、策论等科举考试科目,对其时儒学风向有显著导向作用,二者可谓表里相依。在考察唐宋思想转型问题时,实有必要关注同一时期的科举科目变化。事实上,在金代至元中叶北方儒士群体中,也存在一场从“文”到“道”的重要思想转型,在思想和科举层面均有表现,与唐宋时期的思想转型有诸多共通之处,足以相互印证。金元时期北方的思想转型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本文拟从科举与儒学层面,对此进行研究,并希望回答:程朱理学而非苏学等学说发展为宋代以降主流学术,究竟只是偶然现象,还是符合历史趋势的结果?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其亦可叹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然亦不必辩也,略举其大旨,使后世学者见而嗤之,其时河北之正学且起,不有狂风怪雾,无以见皎日之光明也。
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
全祖望认为建炎南渡后,“学统”随之南迁,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百年不闻学统”,进入儒术中绝的黑暗时代。李纯甫(号屏山居士)等金儒代表人物的学说不值一提,只能作为被后世尊为“正学”的程朱理学北传前的异端学说而受批判。征诸史籍,元代以降文献中有大量儒士批评金朝治下的北方“百年不闻学统”的一类说法。如元儒苏天爵记载:金有国百年,士之为学不过记诵词章而已,其于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赖有一二儒家传其遗业,俾吾道不绝如线,若先生(安熙)之家是也。
中原已为金人有矣。方是时,士之慕功名者溺于富贵之欲,工文艺者汩于声律之陋,其能明乎圣贤之学,严乎出处之义,盖不多见也。我国家治平方臻……有若静修先生(刘因)者出焉……乡间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闻先生讲贯,阅先生论著,始则谤讪,久亦敬服。
苏氏认为,金朝儒士所学不过记诵词章而已,其学只限于注疏和律赋学,至于“性命道德之文”则基本付诸阙如。金代百余年间仅出现安熙(默庵)等个别家族能够世传道德性命之学,使其 在北方“不绝如线”而已。虞集记载北方河东段氏在金元世传“明道之学”:“昔宋失中原,文献坠地。盖为金者,百数十年,材名文艺之士相望乎其间。至于明道正谊之学,则或鲜传者矣。及其亡也,祸乱尤甚,斯民之生存无几,况学者乎?而河东段氏之学,独行乎救死扶伤之际,卓然一出于正。不惑于神怪,不画于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遗风焉。”许有壬《雪斋书院记》云:“金源氏之有中土,虽以科举取士,名尚儒治,不过场屋文字,而道之大者盖漠如也……(赵复)尽出程、朱性理之书付公(姚枢),公得之,躬行实践,发明授徒,北方经学盖自兹始……(姚枢)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许氏认为金代学术原本仅限于科举程文,至于儒学“道之大者”基本付诸阙如,至赵复北上,程朱理学成规模北传,北方儒学面貌才出现大的改观。元初儒士郝经是程朱理学的接受者,他在《读麻征君遗文》一文中概括金代学术:“金源百年富诗文,伊洛一派独征君。”指出金儒擅长诗文,如麻九畴(即麻征君)等研习伊洛理学者寥寥无几,这与上文所论若合符节。除“百年不闻学统”一类记载外,元以降士人还有大量金元北儒“尽弃旧学”的说法。据元代关中理学家同恕记载:祭酒(杨寅)数且喜曰:“先君(杨恭懿)繇侍先祖(杨天德)避乱来归,日从事四子、六经之言,绝口不道诗文。蚤(早)岁有作,皆弃去不录。”
先生(段思温)遂肆力于学,至忘寝食。经史要义,必手籍之。始犹攻辞艺,至是尽弃去,求古圣贤问学之本,究关、洛、考亭之传。聚精会微,以润厥身。菊轩(段成己)深器之,尝曰:“是能世吾家者。”
由以上可知,在同恕笔下,杨恭懿、段思温等金元北儒本不习理学,在接触程朱学说后,立即放弃原有诗赋辞艺,尽弃“旧学”而从事理学修养。与此类似的记载尚有多处,如袁桷述金人徐之纲事云,“金以词赋举进士,君(徐之纲)为词赋大有能名,会金将亡,不得试,作赋说以示学者……上论隋唐曲尽幽眇,久而曰:‘是果为学邪?’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袁桷记载徐之纲弃词赋而修习程朱理学,与杨恭懿等事迹类似。又据《元史·刘因传》:“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刘)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元人刘因初为注疏之学,接触程朱学说后弃旧学而从事理学修养。再如元末潘迪追述元儒伯颜宗道,“时朱子书未大行,学者惟事注疏。(伯颜宗道)从事师数年,终若不自得。一日,有以《四书》见示者,一览,辄欣然曰:‘圣贤之事,其在斯乎!’尽弃其学而学焉。其师见其颖悟,欲教以诗赋,为禄仕计,侯(伯颜宗道)雅不乐”。潘迪记载了伯颜宗道尽弃旧有注疏、诗赋之学而从事理学学习。据以上记载,可知众多元以降儒士对金元学术均有“尽弃旧学”的表述。如杨恭懿、段思温、徐之纲、刘因、伯颜宗道等金元北儒本不习理学,但在接触程朱学说后,立即放弃原有词赋、注疏及记诵之学(“旧学”)而从事理学修养。“百年不闻学统”、“尽弃旧学”两类不同记载共同构成元以降士人对金代学术的“模式化叙事”。在两类记载中,金代儒学原本限于词赋、注疏及记诵之学范畴,除个别一二儒士外,对于义理、性命之学一直乏善可陈。北方儒士在接触到玄奥精深的程朱理学后,遂尽弃旧学而从事代表义理、性命之学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此类“模式化叙事”往往并不准确。如前文叙伯颜宗道事提到其师准备教以诗赋,以从事仕途——在科举长期停废的元代,几无可能。上文主要着眼于学术层面讨论元以降士人对金代儒学的评断,而如前文论说,科举与学术之间有紧密联系,那么金代科举有何特点呢?关于金朝科举,元人王恽简述,“金有国余百年,专以词科取士,曰相曰将,多出此途,议者以‘学涉剽窃,不明义理’为言”以“专以词科取士”笼统概括金代进士科目。金朝科举正式创设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汉进士科分为词赋、经义两科,其中经义科至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废罢,后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始得复科并延续至金亡。金朝前期的词赋、经义两科地位,自然不能不受到皇权影响。关于金熙宗、海陵二帝儒学的授受,史乘中存有相关记载:今虏主完颜亶(金熙宗)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
张用直,临潢人……辽王(完颜)宗幹闻之,延置门下,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海陵即位,召为签书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尝谓用直曰:“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就学,宜善导之。朕父子并受卿学,亦儒者之荣也。”
金熙宗、海陵王分别师从韩昉、张用直等儒士,海陵王太子完颜光英受业于张用直。韩为燕人、张为亡辽上京人,二人授受的内容自然为旧辽学术。众所周知,辽朝进士科以词赋取士,则金熙宗和海陵王父子所传之学当以词赋之学为主,对于经学则或“不能”、或仅“粗有所闻”,因此不难理解金前期海陵王专以词赋科取进士而废经义科的决定。据今人研究,受金章宗“好尚文辞”学术倾向影响,明昌间恢复的经义科很快又在甲次排名、官职除授等方面遭到抑制,以致经义科的地位在金朝中后期始终居于词赋科之下。金朝自正式开科取士直至灭亡,词赋科相比经义科总体上占据优势地位,王恽“专以词科取士”一语概括出进士科目之争的基本史实,的确道出金代科举的大致轮廓。综上,可以看出元以降士人对金代科举和学术的两个基本评判:就整体而论,金朝科举以词赋而非经义为主要进士科目,即“专以词科取士”;在理学成规模北传之前的金代儒学基本均为词赋、注疏及记诵之学,对于义理、性命之学几无建树,即“百年不闻学统”。金代进士科虽就整体而言,可笼统概称为“专以词科取士”,但在金朝历史上,其实尚有一次规模较大的科举改制,虽未能最终改变金朝进士科目的强弱局势,却在较长时期内对“专以词科取士”的科目传统格局造成动摇,进而对金元时期北方学术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这次科举改制目前还未引起学界重视,值得细致研究。首先从南宋时期自金奔宋的“归明人”张棣所撰《金虏图经》一处关键记载说起:《金虏图经》成书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前。海陵朝废除经义科,金世宗朝进士科仅有词赋一科,而据此处语意,世宗当即位后不久便诏令词赋科府试、省试(会试)添加策论考试项目。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句话,还需结合《金史·选举志》中“海陵庶人……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的记载加以说明。上引《金史·选举志》提到海陵王时下诏废除的“策试科”,其实并非进士科目,而是科目内的考试项目。实际上,金人叙述本朝前期“南北选”考试制度时明确表示,“北、南两科同试,皆以策论定高下”,因知金代词赋、经义两科均考试策论。根据宋人洪皓记载,金前期府试,词赋科“试诗、赋、论、时务策”;金人黄久约描述金前期省试有“时行台进士会试上京,犹用旧法试策擢第”云云。以洪、黄之说两相印证可知,金前期词赋科的府试和省试需要考词赋与策论两项。海陵王在废除经义科的同时,将词赋科内的策论项目一并废除。直至金世宗即位,才下令在词赋科的府试和会试中恢复添加策论考试内容。一般来说,论、策两种题型相近,分别以古、今政事经术为考试内容,对于经史知识有较多要求。由是宋人如刘挚称“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材”;马端临谓“诗、赋不过工浮词,论、策可以验实学”。由于试策为新近恢复,且金世宗前期添加的策论考试限于府、会试,未及于最终的殿试环节,故而惯于应试诗赋的金代“场屋举子”似对策、论两场考试仍不太重视。大定十九年(1179),宰相唐括安礼尝议科目,称“臣观近日士人不以策论为意。今若诗、赋、策、论各场考试,文理俱优者为中选,以时务策观其器识,庶得人也”, 劝说世宗加强策论在录取时的权重。不久之后,金廷出现如下对话:(金世宗)谓宰臣曰:“自来御试赋题,皆士人尝拟作者。前朕自选一题,出人所不料,故中选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论为意者,正为此尔。宜各场通考,选文理俱优者。”上曰:“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
为改变科考题易导致“庸流易侥幸”的弊端,世宗终从唐括安礼之议,令殿试亦诗、赋、策、论各场通考。在殿试通考策论后,世宗令“自今府、会两试不须试策”,罢除府、会试的试策内容。除了提升词赋科内策论项目的权重外,大定年间新创的女真进士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策论地位的上升。早在大定四年,金世宗便“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 已经开始将汉文儒经翻译为女真文。之后金世宗接纳耶律履等臣僚建言,诏“以时务策设女直进士科”。大定十三年,首场女真进士科考试举行,试以女真文字,“初立女直进士科,且免乡、府两试,其礼部试、廷试,止对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其考试方式最初仅为试策。至大定二十年增试诗、二十八年又增试论:(金世宗)谕宰臣曰:“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对曰:“《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译《诗》《礼》毕,试之可也。”上曰:“大经义理深奥,不加岁月不能贯通。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后当徐试经义也。”
金世宗不仅令女真进士科增考论题,而且还提出此科将会“徐试经义”。由于以策论考试为主,女真进士科遂得名“策论进士”,之后不久“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允许金朝各族人参加以策论为主的女真进士科考试,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积极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在“庆历新政”中的一个重要诉求,便是“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祝尚书对此指出:“故诗赋、策论之争,实为后来诗赋、经义之争埋下了种子。”诚如其言,继欧阳修之后,王安石推动熙宁变法,正式创立经义进士科,使之在北宋科举中取代诗赋科的地位。祝氏所论从策论到经义的科目演变,为北宋进士科的变迁路向;事实上,金朝经义复科首榜考试虽在章宗明昌二年,但复科诏书在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便已颁降。大定年间以策论复兴为主要内容的科举改制,实为稍后明昌经义复科之基础。除进士科外,大定年间策论及经义之复兴还影响到诸科(杂科)。据成于金章宗朝的李晏神道碑记载:在吏部,一日登对,世宗叹人材难得。公奏曰:“皇统间,诗赋、经义每举放第,两科不下百五十人……又有经童科,总计之不下三百余人。今以词赋一科擢第者常不满百数,是以得人为少。”……上然之,顾大臣曰:“朕屡以问卿等,今得李晏对,使我晓然。”至今上即位,竟复经义、神童两科,又益以宏词、制举,皆自公启之。
这里提到在李晏建言下,章宗朝最终“复经义、神童两科”。揆诸《金史·选举志》有关考试官的记载,“经童,试官一员,隶经义考试院”,可知经童科考试官与经义科同出一院。同属诸科的律科在大定末年亦有改制。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论语》《孟子》以涵养其气度。”甫即皇位的章宗“遂令自今举后,复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府、会试别作一日引试,命经义试官出题,与本科通考定之”。即律科除试律外,也需辅试经义。经童、律科在金朝均属诸科,经童复科、律科增试小义,实可视为策论及经义复兴的余韵。大定科举改制还对晚金科举改制产生影响。金世宗病逝于大定二十九年初,在“好尚文辞”的章宗逐渐掌权后,科举尤重词赋取士,世宗下诏恢复的经义科基本降为词赋科附庸。章宗朝主持贡举的张行简亦独重律赋取士,以致出现“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且数字数与涂注之多寡”的现象,即词赋科考试独重诗赋项目,而视策论如无物。至金宣宗贞祐以降,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等主持贡举后,轻视策论的风气才得以缓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然亦谤议纷纭。然每贡举,非数公为有司,则又如旧矣”。晚金科举改制复以策论为中心,与大定年间如出一辙,但“非数公为有司,则又如旧矣”,其收效不及大定科举改制。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学校自京师达于郡国,专事经术教养,故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明昌以后,朝野无事,侈靡成风,喜歌诗,故士大夫之学,多华而少实。
杨氏以“少华而多实”一语概述大定年间的儒学面貌,与本文所论大定年间策论及经义之复兴若合符节,可以前后印证。大定年间汉进士科虽只有词赋一科存在,但以策论及经义为主要线索,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科举改制:数次提升词赋科内策论考试项目的重要性;创建以策论为主的女真进士科并准备加试经义;下诏恢复经义进士科及经童科;律科增试小义;等等。大定科举改制以策论为中心,虽然未能从根本上突破金朝“以词科取士”的总体科目格局,但在大定一朝近30年间,导致词赋科的传统优势地位产生重要波动,为经义复科奠定思想与制度基础,并对晚金以降的科举制度变迁产生影响。据前文论证,元人“专以词科取士”一语虽总体上概括了金朝科举,但在大定一朝却展现出另一番景象。一般认为,在宋儒赵复被俘北上之后,程朱理学方才成规模地北传;而在此之前金朝治下的北方地区,理学仅有零星传播,未成气候。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全祖望“百年不闻学统”的描述是否符合金代的思想史实呢?在金朝治下的百余年间,北方儒士究竟从何时开始研习义理、性命之学呢?关于金朝学术,翁方纲以“苏学盛于北”予以概括,其意涵虽有多种解释,但文学而非义理、性命之学为北方汉地学术之主流无疑是要义之一,这与全祖望之论似乎颇为相合。然而,金人赵秉文《学道斋记》有如下一段有关金代义理、性命之学的记载,兹不惮繁冗,详引于此:(余)与吾姬伯正父(宗端修)同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他日,余问道于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余但日食二升米,终岁制一缊袍,日旦入局了吾职,不敢欺宾客。庆吊之外,课子孙读书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寻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侪小人于日用事外,所为营营矻矻,计较于得失毁誉之间,不过为身及妻子计而巳(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无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无之;绮绣珠玉玩好之物,伯正父无之;怒气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无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学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学者,何道也?”余笑谢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袜,尝曰:‘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若当诣彼问之。”
此文以“学道”为名,且反复提到同年宗端修(伯正父)“有道”、“知道”云云,修道于寻常日用之际。与此相类,金元史籍中还有大量儒士声称“学道”、“行道”、“斯道”或“吾道”的类似说法。如生活于金中前期的李晏辞尚书省掾时称“一州一县,亦足行道,安能束带抱牍,睢盱作胥吏焉”;承安进士卫文仲,“性好淡泊,读书学道,故仕宦不进”;赵秉文致杨奂书信谓“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等等。蒙元时期北方以吕逊为中心的儒士交游网中,士人常以“斯道”相勉,以期共渡危局。凡此种种,足见“学道”等话语在金蒙之际北儒群体中的长期流行。那么,金蒙北儒所谓儒士“学道”、“行道”等,究竟所学为何呢?三浦秀一、邱轶皓等指出,“道学”一词在金蒙之际常被用以指称当时盛行于北方的全真道。赵秉文所论“学道”是否指道教呢?钩稽金末元初史料,足以否定这种可能。赵秉文撰宗端修墓表称其“生平不喜读佛、道书,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饮酒,屏绝声色”, 明确指出宗氏不喜道教。元好问《中州集》录晚金士人董文甫父子事迹云:(董)文甫字国华,潞人。承安中进士。为人淳质,恬于世味,于心学有所得……子安仁,亦学道。父子尝闲居宝丰,闭户不出,以习静为业,朝夕不继,晏如也。
此处明确提到董氏父子“学道”。刘祁对董氏父子亦有记述,“董治中文甫,字国华,潞州人,第进士……自号无事老人。为人淳谨笃实,学道有得。其学参取佛、老二家,不喜高远奇异……其于《六经》《论》《孟》诸书,凡一章一句皆深思,(思)而有得……其子安仁,传其学”。刘祁提到“学道有得”的董文甫“其学参取佛、老二家”,着力研习儒经,亦可证“学道”并非谓道教。近来思想史研究者逐渐重视作为儒家传统的静坐修身问题。《归潜志》认为,“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君子苟不为世味所诱,何名(之)不成,何节之不立哉?士大夫多为富贵坏了名节……富贵、爵禄,世人所共嗜……苟与世人同,安得为君子。求合于圣贤,必不合于世俗,必欲与世俗合,则于圣贤之道远矣”。不难看出,金人以“道味”与“世味”相对。所谓“世味”, 即功名利禄;“道味”则泛言修身之学。两相结合,可知金代宗端修、董文甫父子等人不宗佛老,却“恬于世味”、“拳拳如奉戒律”、“自号无事老人”以及“闭户不出,以习静为业”等等,其所习之“道”,当属儒家静坐修身之类。生活于金朝中前期的山东儒者王去非,其事迹也可为佐证:先生讳去非……束发知问学……益探六经、百家之言……又取老庄、释氏诸书,采其理要贯穿融会,折诸大中,要本于吾儒修身养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先生有言:“君子得志则行道,不得志则明道。”明道者,不必与邪说辩,辩而胜犹激怒之,其害道滋甚……先生性恬澹,非书无所好。晚岁构堂,曰“因拙”,日以名教自乐,盖得于性命之说为深,死生之际泊如也。
“性恬澹”,“益探六经、百家之言”及“又取老庄、释氏诸书”等描述与宗、董等人如出一辙,可见王氏亦属于“学道”儒士,其修习性命之说即为学道所得。王去非“本于吾儒修身养性之道”,则明证其所行亦为儒家静坐修身之道。除“学道”外,金蒙北儒还时常以与“学道”相通的“心学”相标榜。鲁迅曾论“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 事实上在理学成规模北传之前的金朝,儒士之间已开始讨论“心学”,如李纯甫论“中国心学”、王郁论“孔门心学”等。对此现象,三浦秀一等已有所揭示,不过所论基本皆为金末儒士。实际上,早在金朝中期已有金人开始以“心”、“性”论交。如赵秉文回忆章宗朝与宗端修旧交云:自孔孟之殁几二千年,士大夫以种学绩文为进取之计,干办者称良吏,趋时者为通贤,而不知治心养性之术……大哉心乎,修之可以为贤哲,养之可以塞天地,人知养其身而不知养其心,亦惑矣。公尝语人曰:“凡声色势利之属,皆客气也。人能无以客气害其良心,斯几矣。”故余以为知道。
赵、宗二人已论及“修心”、“良心”,可为明证。又如李纯甫师事史肃(字舜元)而史肃“素尚理性之学”,“屏山学佛,自舜元发之”, 可见生活于金中叶的史,肃也推重心性之学。金人所论“治心养性”复与经学相通,如赵秉文寄书友人言:“足下高才博学,留心经学,研究圣心,宜矣。科举之学,有命存焉,不足置意。”赵氏认为“留心经学”可以“研究圣心”,并以之与尚辞章的科举之学对举,批评后者不足置意。可见至迟从金中叶起,北方儒士已在“学道”的基础上开始谈心说性,逐渐论及性命之学。综上所述,在金朝治下的北方地区,虽未出现如程朱理学一般精深复杂的义理、性命之学体系,但大量儒士以“学道”、“行道”等话语相尚,部分儒士甚至开始标榜“心学”,逐渐走向心性之学。赵复北上之前的北方儒学绝非只停留于词赋、注疏及记诵层面,儒士群体开始追求乃至发明义理、性命之学,由此而言,“苏学盛于北”并不完全符合金蒙时期北方儒学的真相。金代科举和学术对后世有何影响?下文结合元朝科举史上最重要的延祐复科史事予以考察。元朝中叶的延祐复科考试经义,大体以程朱理学著述为标准,“定以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及其师友之说以为国是”基本奠定程朱理学的官方儒学地位,而大力推动复科者则是帝师李孟等人。考之以史,目前可得包括李孟在内10名参与复科之议者。他们的师承交游大多有迹可循,分别考察其学术背景,可以进一步把握延祐复科的学术渊源。(1)李孟为元仁宗之师,深得仁宗信任,出任元朝首科知贡举官,是延祐复科的关键推动者。我们首先考察他的学术背景。据记载,李孟“世为潞州著姓”, 后迁居汉中,师事西轩先生王德舆。王德舆为亡金经童,“丙辰过长安,闻鲁斋许氏以道学鸣……聚周、程、张、朱氏书而探讨之,得其义理之精微”, 在元宪宗朝已受许衡影响而服膺程朱理学。王德舆“居汉中三十年,郡人咸师表之”, 为元代汉中理学奠基人。同出汉中的元中期理学家蒲道源即屡从王德舆游,深受其影响,并与王氏一族结为姻亲。师事王德舆的李孟又与蒲道源为世交。蒲氏曾自叙:“昔吾与秋谷秦国公(李孟)有里闬陪从之旧,其先正韩国忠献公(李唐),吾童时所拜事者。”蒲道源童时即拜事李孟之父李唐,而李孟二侄李胤宁、李胤家又为蒲氏门人。蒲氏文集中有大量与李孟交游的记述,诸如唱和、祝寿、贺得子等,足见蒲、李两人的密切关系。根据李孟与王、蒲二人的交往,可判定李孟为受汉中理学影响之儒士。(3)程钜夫,江西南城人。《元史》记载:“诏钜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参知政事许师敬议行贡举法。钜夫建言:‘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钜夫草诏行之。”可见李孟、许师敬及程钜夫三人是延祐复科的主要倡议人。程钜夫师从徽庵先生程若庸,与吴澄同门,为朱熹四传弟子。(4)伯帖木儿,西域哈剌鲁人,在元朝属色目人。目前尚不详师承,但据其家传,他曾经向元仁宗奏言“在陕西见老儒郭松年有文章议论……其次若同宽甫、贾文器、侯伯正辈,学问政事皆有可采”,向仁宗推荐关陕诸儒。可知伯帖木儿与同恕(字宽甫)等关中理学儒士相交。(5)陈颢,清州(今属河北)人。《元史》本传记载:“稍长,游京师,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门。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诸国语,颢兼习之。”《宋元学案补遗》列之为“鹿庵门人”, 即王磐(号鹿庵)弟子。王磐礼敬许衡,尊崇北传之理学;不过,“熟金典章”的王磐“既冠,闻偃城麻征君九畴为时名儒,裹粮往从之学,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 在金代从学以经义之学闻名的麻九畴,进而研习理学,亦有金源学术渊源。(6)王约,真定(今属河北)人。《元史》本传云:“从中丞魏初游,博览经史,工文辞,务达国体,时好不以动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学士王磐荐为从事。”可知王约从游魏初,并见知于王磐。《宋元学案补遗》将之归为“魏氏门人”。魏初少时从亡金儒士庸斋先生杨时煦学。至元间“按部自雍还”,始得与王德舆相识,“先生巍冠博褐,进止舒徐,其容庄、其辞温,蔼然程朱家语录中人也,用是尝侍几杖十有五年”,又从王德舆问学15年,与王氏父子交好。如是,王约亦为杨时煦与王德舆再传。(7)刘赓,洺水(今属河北)人。据刘赓自述:“尝师事鹿庵先生,得告还东平,前诸生,谓公(胡祗遹)曰:‘敢以是数后进累吾绍开(闻)。’且命之罗拜,公避之。鹿庵良久曰:‘以师友之间待乎?’公遂诺焉。”可知刘赓先后师事王磐、胡祗遹。《宋元学案补遗》列之为“鹿庵门人”。刘赓也是佚庵先生刘肃之孙。《元史》记载,刘肃“尝集诸家《易》说,曰《读易备忘》”,刘秉忠之弟刘秉恕“年弱冠,受《易》于刘肃,遂明理学”。可见刘肃以精通《易》经义理闻名,刘赓或亦受到家学影响。(8)吕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为许衡门人,又“日与韩公择、萧公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为许衡门人,又“日与韩公择、萧公 、同公恕讲论道义,从容函丈”是典型的理学北传接受者。(9)元明善,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早年游学南方,从学吴澄,“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子弟礼,终其身”。(10)贯云石,元初名臣阿里海牙孙。据欧阳玄记载,贯云石“北从承旨姚文公学”。贯云石从学姚燧,是为许衡再传。根据以上考察,不难看出,具有金代学术背景的汉人儒士是延祐复科的关键推动者。推导延祐复科的诸人除普遍受到理学北传的影响外,尚有李孟、陈颢、王约、刘赓等近半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存有旧金经学渊源。在前文中,我们先后讨论了金代至元中叶大定科举改制、晚金科举改制与延祐复科三次科举改制。金代文献传世者为数甚为有限,但爬梳史料后发现,如果跨越断代藩篱,则金至元中叶时期三次重要的科举改制之间仍隐有草蛇灰线可寻。首先,李晏本为金前期经义进士,他在大定科举改制中推动世宗诏令经义复科,赵秉文、李纯甫等又在晚金科举改制中推动策论复兴。赵秉文为大定年间进士,与李采(李纯甫之父)、宗端修同年,该榜御试读卷官即李晏。按李晏被时人尊为“吾道之主盟”;赵秉文作诗“善哉刘与李,斯文见典型”,奉李晏之子李仲略为“斯文”典型。可见李晏父子为北方“学道”儒士中的先进。其次,李晏推动金朝经义复科,而主持晚金科举改制的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均为金经义进士,其改制方向与大定改制一致,且他们皆为“学道”之儒。再次,李晏即泽州高平人,推动金朝经义及经童复科,他所授经学在金代对高平乃至泽潞地区有较大影响,高平可谓金朝经学渊薮。李孟师从王德舆,王氏为亡金经童,又“世为濩泽高平人”, 与李晏为同乡。李孟推动延祐复科,认同“试艺者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 与大定、晚金科举改制方向基本相同。结合以上三点,可知大定科举改制、晚金科举改制与延祐复科的倡导者,均为北方标榜“学道”之儒士。元朝中叶延祐复科的科目倾向与大定、晚金两次改制一脉相承,一方面受到南方理学北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金代科举改制与北方儒学演进的长远承续,堪称北方新、旧儒学汇流的结果。通过前文考论,可对金至元中叶的科举科目流变和学术演进的历史产生新认识。如果将研究视线进一步延展,以之与唐宋时期思想转型的历史背景相比较,从比较中探寻规律,将对这段复杂的历史形成更深层理解。下文以上表所列有关唐宋思想转型的9项重要历史背景为线索,结合科举制度和儒学演变两个方面,来对比阐释唐宋与金元两段时期的思想转型。第(1)—(4)项已见于前文讨论;关于第(5)—(9)项,尚需阐说。第(5)项,中唐至北宋时期发生“古文运动”,这场文学运动排斥四六骈文、以古文相号召,充满治道关怀。在金末元初的北方中国,则出现一场“古学运动”,同样力排四六文,以古学相号召,追求治道。 第(6)项,在唐宋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儒者开始尚“统”,最初文统与道统不分,并纳汉唐儒士入统绪之内,此即朱刚所论理学道统论出现之前的“道统论第二种形态”。金元北儒标榜“中州文统”,文道兼取,包容汉唐,亦属“道统论第二种形态”。第(7)项,由于《易》的深奥复杂,向来被儒士视为“性与天道”学说之渊薮。宋代理学兴盛前,朝野儒士解《易》者蜂起,为其后性命之学的勃兴奠定基础。与之相似,《易》学在金至元中叶同样深受北方儒士重视,金蒙之际北方出现许多解《易》作品。第(8)项,在北宋理学初兴之际,儒士领袖如王安石、程颐等皆援佛老入儒,以期构建起可与佛老心性学说相媲美的儒家性命体系。晚金儒学领袖赵秉文、李纯甫等同样对佛老之学产生浓厚兴趣:赵秉文“上至六经解,外及浮屠、庄老、医学(药)、丹诀,无不究心”;李纯甫“晩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藁’”也开始尝试吸收佛老思想。第(9)项,荆公新学重视“心”的建构,是心性学说在北宋发展的代表,在熙丰年间成为官方儒学;靖康之变后新学日渐式微,程朱理学继之兴起,程、朱仍以性理为基础构建理学体系,在晚宋亦获得官方承认。金后期如李纯甫、王郁等部分儒士已明确提出建构吸化佛老的“中国心学”、“孔氏心学”,此后又有赵复等南方理学家北上传学,精深的程朱理学在北方成规模传播,至元中叶延祐复科,以心性道德为核心的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方儒学。研究者指出,金朝在教育、文化等不少方面有中古向近世转型的遗留痕迹。综合以上可知,在(1)—(9)项特征上,金至元中叶北方儒士群体的思想转型与此前唐宋时期的思想转型相近,实可称之为唐宋思想转型的另一条轨迹。据此可知,赵复、许衡等传播理学之前的金代儒学,略同于北宋嘉祐之际的儒学发展面貌。这一时期的北方儒士立足治道、号召古学,并开始探研心性之学。北宋以降,理学出现并渐次发展为宋元明清的主流儒学形态,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程朱理学出现于北宋后期,以心性道德为核心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为何以内向的心性之学为根基的宋明理学会成为宋代以降的主流学术?包弼德研究唐宋思想转型提出,程朱理学在当时是一种反主流学术思潮的新学说,“与始自8世纪的思想潮流格格不入”,程学而非具有多样性的苏学成为后世主流儒学“并不是早期思潮的一个必然和逻辑的结果”,亦即具有偶然性。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曾假设南宋以吕祖谦为代表人物、更具包容性的婺学取代朱子学成为主流儒学,后世历史面貌将大不相同。对于理学成为宋代以降主流学术的内在思想动因,非本文所能及;但根据本文对两条唐宋思想转型轨迹的研究可知,从“文”到“道”的唐宋思想转型不仅发生于唐宋时期,也同样发生于金至元中叶,求“道”、推行科举经学化改制,并统摄佛老学说,从而建构儒家心性学说体系的新儒学兴起,是唐宋以降的历史演变趋势。程朱理学无论在求“道”、推行科举经学化改制或统摄佛老方面,都胜过苏学及婺学等学说,因此更符合唐宋思想转型这一历史潮流的理学,成为宋代以降的主流儒学并非偶然。
、同公恕讲论道义,从容函丈”是典型的理学北传接受者。(9)元明善,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早年游学南方,从学吴澄,“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子弟礼,终其身”。(10)贯云石,元初名臣阿里海牙孙。据欧阳玄记载,贯云石“北从承旨姚文公学”。贯云石从学姚燧,是为许衡再传。根据以上考察,不难看出,具有金代学术背景的汉人儒士是延祐复科的关键推动者。推导延祐复科的诸人除普遍受到理学北传的影响外,尚有李孟、陈颢、王约、刘赓等近半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存有旧金经学渊源。在前文中,我们先后讨论了金代至元中叶大定科举改制、晚金科举改制与延祐复科三次科举改制。金代文献传世者为数甚为有限,但爬梳史料后发现,如果跨越断代藩篱,则金至元中叶时期三次重要的科举改制之间仍隐有草蛇灰线可寻。首先,李晏本为金前期经义进士,他在大定科举改制中推动世宗诏令经义复科,赵秉文、李纯甫等又在晚金科举改制中推动策论复兴。赵秉文为大定年间进士,与李采(李纯甫之父)、宗端修同年,该榜御试读卷官即李晏。按李晏被时人尊为“吾道之主盟”;赵秉文作诗“善哉刘与李,斯文见典型”,奉李晏之子李仲略为“斯文”典型。可见李晏父子为北方“学道”儒士中的先进。其次,李晏推动金朝经义复科,而主持晚金科举改制的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均为金经义进士,其改制方向与大定改制一致,且他们皆为“学道”之儒。再次,李晏即泽州高平人,推动金朝经义及经童复科,他所授经学在金代对高平乃至泽潞地区有较大影响,高平可谓金朝经学渊薮。李孟师从王德舆,王氏为亡金经童,又“世为濩泽高平人”, 与李晏为同乡。李孟推动延祐复科,认同“试艺者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 与大定、晚金科举改制方向基本相同。结合以上三点,可知大定科举改制、晚金科举改制与延祐复科的倡导者,均为北方标榜“学道”之儒士。元朝中叶延祐复科的科目倾向与大定、晚金两次改制一脉相承,一方面受到南方理学北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金代科举改制与北方儒学演进的长远承续,堪称北方新、旧儒学汇流的结果。通过前文考论,可对金至元中叶的科举科目流变和学术演进的历史产生新认识。如果将研究视线进一步延展,以之与唐宋时期思想转型的历史背景相比较,从比较中探寻规律,将对这段复杂的历史形成更深层理解。下文以上表所列有关唐宋思想转型的9项重要历史背景为线索,结合科举制度和儒学演变两个方面,来对比阐释唐宋与金元两段时期的思想转型。第(1)—(4)项已见于前文讨论;关于第(5)—(9)项,尚需阐说。第(5)项,中唐至北宋时期发生“古文运动”,这场文学运动排斥四六骈文、以古文相号召,充满治道关怀。在金末元初的北方中国,则出现一场“古学运动”,同样力排四六文,以古学相号召,追求治道。 第(6)项,在唐宋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儒者开始尚“统”,最初文统与道统不分,并纳汉唐儒士入统绪之内,此即朱刚所论理学道统论出现之前的“道统论第二种形态”。金元北儒标榜“中州文统”,文道兼取,包容汉唐,亦属“道统论第二种形态”。第(7)项,由于《易》的深奥复杂,向来被儒士视为“性与天道”学说之渊薮。宋代理学兴盛前,朝野儒士解《易》者蜂起,为其后性命之学的勃兴奠定基础。与之相似,《易》学在金至元中叶同样深受北方儒士重视,金蒙之际北方出现许多解《易》作品。第(8)项,在北宋理学初兴之际,儒士领袖如王安石、程颐等皆援佛老入儒,以期构建起可与佛老心性学说相媲美的儒家性命体系。晚金儒学领袖赵秉文、李纯甫等同样对佛老之学产生浓厚兴趣:赵秉文“上至六经解,外及浮屠、庄老、医学(药)、丹诀,无不究心”;李纯甫“晩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藁’”也开始尝试吸收佛老思想。第(9)项,荆公新学重视“心”的建构,是心性学说在北宋发展的代表,在熙丰年间成为官方儒学;靖康之变后新学日渐式微,程朱理学继之兴起,程、朱仍以性理为基础构建理学体系,在晚宋亦获得官方承认。金后期如李纯甫、王郁等部分儒士已明确提出建构吸化佛老的“中国心学”、“孔氏心学”,此后又有赵复等南方理学家北上传学,精深的程朱理学在北方成规模传播,至元中叶延祐复科,以心性道德为核心的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方儒学。研究者指出,金朝在教育、文化等不少方面有中古向近世转型的遗留痕迹。综合以上可知,在(1)—(9)项特征上,金至元中叶北方儒士群体的思想转型与此前唐宋时期的思想转型相近,实可称之为唐宋思想转型的另一条轨迹。据此可知,赵复、许衡等传播理学之前的金代儒学,略同于北宋嘉祐之际的儒学发展面貌。这一时期的北方儒士立足治道、号召古学,并开始探研心性之学。北宋以降,理学出现并渐次发展为宋元明清的主流儒学形态,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程朱理学出现于北宋后期,以心性道德为核心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为何以内向的心性之学为根基的宋明理学会成为宋代以降的主流学术?包弼德研究唐宋思想转型提出,程朱理学在当时是一种反主流学术思潮的新学说,“与始自8世纪的思想潮流格格不入”,程学而非具有多样性的苏学成为后世主流儒学“并不是早期思潮的一个必然和逻辑的结果”,亦即具有偶然性。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曾假设南宋以吕祖谦为代表人物、更具包容性的婺学取代朱子学成为主流儒学,后世历史面貌将大不相同。对于理学成为宋代以降主流学术的内在思想动因,非本文所能及;但根据本文对两条唐宋思想转型轨迹的研究可知,从“文”到“道”的唐宋思想转型不仅发生于唐宋时期,也同样发生于金至元中叶,求“道”、推行科举经学化改制,并统摄佛老学说,从而建构儒家心性学说体系的新儒学兴起,是唐宋以降的历史演变趋势。程朱理学无论在求“道”、推行科举经学化改制或统摄佛老方面,都胜过苏学及婺学等学说,因此更符合唐宋思想转型这一历史潮流的理学,成为宋代以降的主流儒学并非偶然。